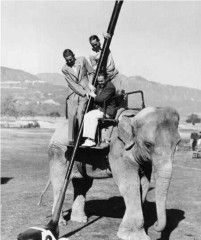大學裏麵“尷尬”的文科:今天我們為什麼依舊需要人文精神?(2)
而吉見先生卻試圖為之一辯。對於主流社會相關議論中的關鍵詞、理科思維下的單一尺度——“創新”,他援引馬克斯·韋伯的“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提出了異議,他將廣義上的“理科”與“文科”的意義維度區分為“完成目的的有用性”和“創造價值的有用性”。其中,前者“隻針對事先給定的目的才有效”,“如果目的或價值尺度本身發生了變化,那麼以為‘有用’而做出的解答,將變得毫無價值”,因此也“無法從內部突破既有體係”;而後者“則要求具有將那些可能在較長時間段中發生變化的多元價值納入視野的能力”,而“在多元的價值尺度中,為了在每一種具體情況下用最佳的價值尺度,就需要與各種價值尺度均保持一定距離,采取批判的態度。深陷於某一個價值尺度,將失去應對新變化時的靈活性。”這一區分中至少暗含著文科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兩種可能性,它可以象征想象力,更應是防波堤。吉見在可比的意義上,通過對日本的索尼公司與美國的蘋果公司的比較,指出“日本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缺乏在曆史大潮中改變價值尺度,並大膽預測未來的力量。”而陳平原的憂慮和提醒則更為普遍的現實性。他在討論人文與科技的關係時表示,“技術進步無法阻擋,但其對於人類思想及道德的挑戰不能忽視,起碼必須未雨綢繆,不能任憑某種科技(比如信息科技)單兵突進。”(陳平原:《理直氣壯且恰如其分地說出人文學的好處》,收入《文學如何教育:人文視野下的文學教育》,北京:東方出版社,2021年3月,第27頁。)這些年數字化、人臉識別技術、AI、人工智能摧枯拉朽的迅猛發展,而其問題在近年來也已逐漸凸顯,當此時也,“文科何為”值得重思。

電影《墊底辣妹》劇照。
作為文科出身的東京大學的副校長,吉見試圖回應的問題,毋寧說也正是我們當下不得不直麵的問題——文科該如何活下去?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這個問題與其說是出給國家、社會、學生的問題,不如說是出給教育管理者們的問題,他們首先要麵對的是,在已身在“創新”風潮中的文科教師、學者們的生存問題和包括資源分配等與學科存亡息息相關的關鍵問題。作為一個從事日本文史教學與研究的“文科”從業者,自然不難理解其良苦用心,且心同此心、感同身受;甚至不妨明言,文科危機,四海攸同。不過,這裏似乎依然有兩個問題需要仔細推敲、斟酌。首先,這種寬泛的“文科”“理科”區分是否會在“基礎學科”與“應用學科”的意義上混淆了理科與工科醫科、人文學與社會科學的使命和功用。前文談到的“強基計劃”,在政策製定者那裏,正是“要突出基礎學科的支撐引領作用,重點在數學、物理、化學、信息學、生物學及曆史、哲學、古文字學等相關專業招生”。基礎學科的意義需要以官方政策強力傾斜支撐本身,其背後不正是人文學科和理科被認為“短期無用”嗎?在這一點上,日本與中國別無二致,吉見就坦率地指出,“‘掙錢的理科’與‘不掙錢的文科’這一對立成為了世間的‘常識’,這才是隱藏在本次‘廢除文科學部問題’引發的事態背後的真正的根本性問題。”其次,吉見指出,今天日本的“重理”路線實則是戰時總力戰體製、“選擇與集中”政策的慣性延續。這一戰時日美爭勝的邏輯轉而在當下提高日本大學“國際競爭力”的語境下得以繼承,此說堪稱洞見。而在批判理科式“完成目的的有用性”時,作者給出了兩個案例:“日本經曆了這樣的教訓,戰爭時一說‘鬼畜美英’,大家都眾口一詞痛斥‘鬼畜美英’,戰後一說‘高速增長’,大家又都朝著‘高速增長’奮力疾行。”在這一論述中,戰後與太平洋戰爭時期似乎共有某種因理科式“工具理性”而形成的目的批判、價值相對自覺之缺失。關於前者,作者在本書第一章做了具體的展開:
二戰中的日本抱著戰勝美國這一明確的目的,以能夠直接貢獻於此的理工科應用型學問為中心,全力動員大學的知識資源支撐戰爭,結果卻是一切化為灰燼,國民遭受滅頂之災。視目的為既定要求,一味追求作為工具的有用性——從這樣的思考模式之中,無法產生“其實戰勝美國是根本不可能的”這樣對目的本身進行客觀批評的視點。在那個時代,擔負知識生產責任的大學本應該做的,不是跟風設立有助於提高軍事技術水平的研究所,而是勇敢地指出大家正在追求的目標從根本上是錯的,從而轉換價值標準,確定新的目標,開創出新的時代。
在目的-價值二元論中,吉見先生以“日本戰勝美國是否可能”的問題(而非近代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作為批判理科“目的有用論”的批判似乎暗含著“如若可能,便可支持”的邏輯是否妥帖(在戰時日本,理科以科學技術殺人,而文科用思想文筆殺人,雖強度、烈度有別,但在“目的/價值給定”的意義上別無二致,“筆部隊”此之謂也)且按下不表,需注意的是,這一觀念實則是以流動性的“多元價值”之存在空間、以“價值有用”為追求的文科之批判空間為不言自明的前提,但是,這一先決條件本身卻並不是自明的。而若價值唯一,那麼質疑與批判是否可能,對於明治以降的日本曆史而言,結論是顯而易見的。既然在某些特定的曆史語境下,價值難以多元,如此則從多元價值的可能性上討論文科存在的價值恐怕就有些勉為其難。並非是要徹底否認吉見的立論基礎、求全責備,因為此書原本便是在“‘歐美列強’的全球性學術霸權不斷推進的當下”、以日本民眾為預設讀者,而隻想強調,落實到實踐層麵,這一論斷並不具備超越時代和國界、可操作的普遍性。

日劇《龍櫻2》劇照。
另外,並非有意潑冷水,吉見先生的預設讀者是日本的一般民眾,大概率事件是,在觀念層麵人們會認為先生所言不無道理,但卻無關自己的現實選擇。盡管如此,這種發聲依然是必要的、可貴的。我們似乎已經習慣了在學術共同體內部不厭其煩地主張文科的價值,這顯然是搞錯了對象,實則無需多言,因為我們需要著意對話的對象應是“圈外人”——包括政府官員、一般民眾乃至行外專家,因為他們或許在更大程度上左右、影響著文科的當下命運和未來走向。陳平原教授便曾明言其近年來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向圈外人發言,讓他們明了人文學的意義;或者說,如何向已達成某種默契的‘社會共識’挑戰,證明人文學的存在價值及發展空間”,強調“人文學者要學會理直氣壯且恰如其分地、公開地、大聲地說出人文學的好處、貢獻與重要性”。茶杯裏的風波、微信群裏的牢騷於事無補,抬頭看路,我們需要更多的陳平原。
有形與無形
大學、學科是一個曆史性產物,自有其壽命和限度,人類社會對大學與學科認知進程之嬗變無疑也是不同時期、參數不斷變化的前提下,權力、社會、市場與人等諸多要素綜合約束、協商、作用的結果。有時,究竟是社會誤解、拋棄了大學,還是大學中人錯付了時代、誤判了社會,誰辜負了誰,還真難說。但有一點是確定的,那就是對大學、對學科做“去曆史化”理解是要不得的,而基於現實困境的曆史回望將賦予當下觀察以必要的曆史感覺。吉見敏銳地指出,“日本的大學被‘全球化’‘數字化’‘少子高齡化’三大浪潮席卷。這三大浪潮使得大學、學問以及社會的存在方式發生了三重變革,任何一所大學都再也無法依靠既有的方式繼續生存了。也許是為了應對社會流動性、無邊界化以及不穩定性等一係列問題,大學知識生產的存在方式也在發生變化”,並將其主要特征總結為知識的市場化、全球化、數字化和複雜細分化。

日劇《麻辣教師G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