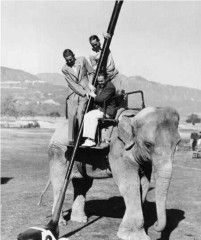分成兩半的嚴複:被誤解的“天演”,被銘記的“富強”(2)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此時的嚴複都像是一個鬱鬱不得誌的憤懣士子,如果再加上之前連續四次科舉不第,更讓他心灰意冷,萌生退意。如果嚴複按照信中所述,就此南歸,甚至徹底歸鄉,那麼他就會像千千萬萬齎誌以歿的人一樣,成為近代史上的失蹤者。但是,僅僅在他那封心灰意冷的信發出的20天後。1895年2月4日天津《直報》刊出了他撰寫的《論世變之亟》,將他猛然推上了曆史的前台。
“嗚呼,觀今日之世變,蓋自秦以來未有若斯之亟也。夫世之變也,莫知其所由然,強而名之曰運會。運會既成,雖聖人無所為力,蓋聖人亦運會中之一物。既為其中之一物,謂能取運會而轉移之,無是理也。”
開篇讀來,確實縱橫捭闔,頗具氣象。熟悉明清八股策論的文士,在看過這段之後,或許會撚須哂笑:此種大談世變、運會、聖人的文辭,與考場上用以吸引考官注意而故作張揚的八股破題幾乎別無二致。但這篇文章真正的刀鋒隱藏在第二部分,對中西異同的比較:
“嚐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複衰,既治不可複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
嚴複幾乎毫無顧忌地將中西之間的區別全然對立起來。而在後文中,嚴複更對中國所尊奉的古代聖人加以批判,他先是故作理解聖人之心,推想古賢先聖是因為擔心“物不足則必爭,而爭者人道之大患也”,所以刻意用“止足為教”,教導百姓安分守己,避免競爭。但聖人敉平競爭之用意,最終導致的結果卻是“民智因之以日窳,民力因之以日衰,其究也,至不能與外國爭一旦之命”。
嚴複這番話幾乎相當於將聖人之術直呼為愚民之術。盡管他在文中將中西文明進行比較時,尚且半遮半掩地寫道“吾實未敢遽分其優絀也”。然而隻要參考中西對戰的勝敗現實,那麼就可以明了,在前麵列舉的中西方種種不同之處,嚴複道破了中西競爭一敗一勝的原因所在:
“中國最重三綱,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國親親,而西人尚賢;中國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國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國貴一道而同風,而西人喜黨居而州處;中國多忌諱,而西人眾譏評。其於財用也,中國重節流,而西人重開源;中國追淳樸,而西人求歡虞。其接物也,中國美謙屈,而西人務發舒;中國尚節文,而西人樂簡易。其於為學也,中國誇多識,而西人尊新知。其於禍災也,中國委天數,而西人恃人力”。
嚴複最後開出了他的藥方,“夫士生今日,不睹西洋富強之效者,無目者也。謂不講富強,而中國自可以安;謂不用西洋之術,而富強自可致;謂用西洋之術,無俟於通達時務之真人才,皆非狂易喪心之人不為此”。
唯有直麵西方列國富強的現實,去學習西洋富強之術,來拯救行將“亡國滅種,四分五裂”的中國沉屙。
分成兩半的嚴複:被誤解的“天演”,被銘記的“富強”
世變
《論世變之亟》隻是嚴複送上的一杯開胃酒,但行文之中那種對中國古聖先賢近乎劍拔弩張的冒犯,足以引人矚目。而他在一個月後刊發的《原強》才是真正的饕餮大餐。《原強》文中對達爾文的進化論與斯賓塞的社會學進行了大張旗鼓地闡發與推崇。
盡管早在十五年前,西洋來華傳教士們,就在諸如《萬國公報》《佐治芻言》之類的刊物和譯作中涉及達爾文的進化論學說,但真正將其推廣遍及閭巷的宣傳大師,仍然非嚴複莫屬。嚴複的本領在於他特別善於從浩繁的學術論著和觀點中,提煉出自己需要的觀點,鍛造成格言警句,以不容置疑的口吻灌輸給渴求新知的讀者。達爾文的進化論被嚴複簡化了兩個關鍵篇章《爭自存》與《遺宜種》:
“所謂爭自存者,謂民物之於世也,樊然並生,同享天地自然之利。與接為構,民民物物,各爭有以自存。其始也,種與種爭,及其成群成國,則群與群爭,國與國爭。而弱者當為強肉,愚者當為智役焉。”
嚴複將達爾文的進化論提煉為一種萬物間為了生存無休止的爭鬥,弱肉強食乃是進化的公理。而此一公理,“微禽獸為然,草木亦猶是也;微動植二物為然,而人民亦猶是也”——進化論弱肉強食的公理不僅自然界如此,同樣也施之於人類社會,“人民者,固動物之一類也”。
至於斯賓塞(嚴複在《原強》中譯為“錫彭塞”),嚴複則以“群學”來命名其學說,如此他便可以托以荀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能群也”進行適應中國傳統觀念的闡發。嚴複將斯賓塞的學說與傳統四書中的《大學》“誠正修齊治平之事”相提並論,而“第《大學》引而未發,語而不詳。至錫彭塞之書,則精深微妙,繁富奧衍”——在嚴複心中,斯賓塞的學說幾乎被視為超越中國傳統經典的存在。
但嚴複對群學的歸納,卻不像對達爾文進化論的歸納一般精辟概要,而是用諸如“天下沿流溯源,執因求果之事,惟於群學為最難。有國家者,施一政,著一令,其旨本以坊民也”之類的言辭,一再揄揚斯賓塞的學說:
“嗚呼!美矣!備矣!自生民以來,未有若斯之懿也。雖文、周生今,未能舍其道而言治也!”
為何會如此呢?從某種意義上說,或許是因為嚴複對斯賓塞的學說太過了解,以至於他意識到這一體係龐雜的學說難以像進化論一樣籠統概括。而另一方麵,他真正想要從中提取的精髓,隻在於兩點:一是人民作為組成社會(群)的有機體,唯有提高人民整體的素質,才能達成社會的總體進步。所謂“至於其本,則亦於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開,民力日奮,民德日和,則上雖不治其標,而標將自立”。
另一方麵,群學之所以謂之“群”,乃是與進化論相輔相成,在這個弱肉強食為公理的世界上,個體的消滅在所難免,但是作為群的種族-國家卻可以在競爭中得以長存。因此,作為個體,在為了群體利益而提升自我素質的同時,也要時刻做好舍己為群的準備。

《世界進步之比較》,出自晚清《神州畫報》。
在《原強》刊發的十天後,嚴複發表的《辟韓》可以被視為對《原強》的進一步闡發。但這一次,他徑直將中國世代尊奉的君臣之道掀翻在地,嚴複指出民眾本能自己相生相養,卻被君主欺奪患害。因此,“君臣之倫,蓋出於不得已也”。中國之所以現而今不能棄君臣之倫的原因,隻是“其時未至,其俗未成,其民不足以自治也”,因此一旦人民足以自治,君主自然要被消滅。而中國的情勢,雖然因為民缺乏自治能力,不得已有君主。
但“西洋之民,其尊且貴也,過於王侯將相;而我中國之民,其卑且賤,皆奴產子也”——暴橫的主子驅使一群順從的奴隸與西洋各國的公民競爭戰鬥,“彼其民為公產公利自為鬥也,而中國則奴為其主鬥耳。夫驅奴虜以鬥貴人,固何所往而不敗?”
如此看來,嚴複儼然是一位民治主義者,相信唯有提高民智、培育民德、抒發民力,依靠民眾自治才能真正達到進化之境,在進化論宰製下弱肉強食的競爭大戰中取得勝利。
這固然是一個美好的理想,然而,我們卻不得不提出這樣的問題:誰來培育擁有自治能力高素質的民眾呢?當這群各具才智德行的民眾意見出現分歧時,又該最終聽誰的意見呢?
嚴複無法想象一個個體擁有了聰明才智和美好的德行,卻如同一盤散沙一樣,不願為國效力,參與到弱肉強食的競爭中去。或許,在他看來,進化的結果就是人類走向和諧統一的大群——盡管後者可能也是他所意想未到的,因為那畢竟太過遙遠,而眼前最重要的目標是富強。
《論世變之亟》《原強》與《辟韓》可以說是嚴複開出的富強良方。這三篇論說已然讓其名聲大噪。但最終將嚴複的名字牢牢釘在近代史的萬神殿中的那根金釘,乃是他在次年翻譯完成的《天演論》。
分成兩半的嚴複:被誤解的“天演”,被銘記的“富強”
天演
“物競天擇,適者生存。”
《天演論》將這八字格言銘刻在幾代中國人的腦海中。以至於提及這本書,人們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八個字。在某種程度上,嚴複期望通過此書表達的理念,幾乎已經在他發表的三篇論說《論世變之亟》《原強》與《辟韓》中闡發殆盡,特別是《原強》,幾乎可以作為《天演論》的縮略版來閱讀。
對今天的讀者來說,因為這本書的譯筆太過古奧典雅,以至於除了專門的研究者外,幾乎無人真正完整地閱讀過這本書。然而唯有精讀,才能發現嚴複在這本譯作中埋下的玄機。

《赫胥黎天演論》,慎始基齋版,這是嚴複親自校訂的《天演論》最完備的一個版本。
作為一名譯者,首先要求的應該是信實,即使文筆不逮,也應盡量做到符合原意。如果按照此一標尺進行量度,就會發現嚴複的《天演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不合格的譯作。為了遷就自己的觀點,他不惜篡改原著者赫胥黎的本意。赫胥黎是達爾文最忠實的傳揚者,對達爾文進化論在世界範圍內的推廣居功厥偉。但也正因為赫胥黎對達爾文的學說理解深刻,因此,他才不會同意同時代的人將達爾文對自然界的進化理論的研究,推而廣之,放諸人類社會,他更不會認可動物界的弱肉強食可以作為人類社會恃強淩弱的公理。
在原著的第七章中,赫胥黎寫道:
“最強者和自我求生力最強者,總是趨於蹂躪弱者。”
然而這句話卻被嚴複改譯為:
“故善保群者,常利於存;不善保群者,常滅於鄰,此真無可如何之勢也。”
仿佛赫胥黎認為人類社會結成群體的目的就是為了在無法避免的弱肉強食中競爭求存。
在原著的第五章中,赫胥黎寫道:
“不幸的是,這個形容詞(人類的純粹理性)的意義經曆了這麼多的改變,以至於把它應用到為了共同的善而命令人犧牲自己的理性上去,現在聽起來幾乎是有點可笑了。”
但對嚴複來說,赫胥黎的這一觀點毫無疑問會讓自己這個舍己為群的主張者感到不適,因此,他完全扭曲了這句話的意思,變成了:
“蓋惟一群之中,人人以損己益群,為性分中最重要之一事,夫而後其群有以合而不散,而日以強大也。”
赫胥黎的本意就這樣被嚴複通過錯譯的方式被完全扭曲,嚴複也樂於在書中的按語裏引出自己所欣賞的斯賓塞,並用他的觀點修正,甚至是反駁赫胥黎的觀點。在嚴複看來,斯賓塞的群學完美詮釋了群體利益與個體利益是合二為一的,隻要能夠使群中個體相信自己是群中一員,那麼他自然而然就會將群體利益視為自己的利益,並為了群去自我犧牲——尤其是在危急存亡之時,沒有了群體的庇護,個體又該如何生存呢?
嚴複的用意可以理解,他所身處的時代正是危急存亡之秋,在世界種群競爭之中,中國已經落於下風,麵臨亡國滅種的危險。
這也就是他的係列論說的最後一篇題為《救亡決論》的原因所在。不過饒具意味的是,這篇闡發救亡圖存方法的文章,實際上卻是一枚扔向八股取士科舉製度的炸彈。嚴複在論說中抨擊八股“錮智慧”“壞心術”“滋遊手”。這篇文章在1895年5月1日開始連載刊發的目的恐怕也沒有那麼簡單,因為次日便是全國各省舉子齊聚北京參加會試的日子。而1895年的這場會試,注定會在近代史上留下重重的一筆,一千餘名舉子痛於甲午戰敗之恥,聯名上書,要求變法。

描繪公車上書情景的《伏闕陳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