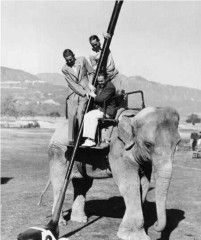分成兩半的嚴複:被誤解的“天演”,被銘記的“富強”(3)
身在北京側近天津的嚴複,自然不會不知道這起事先張揚的公車上書。他的《救亡決論》可以說正中這些科舉考生的下懷。從某種程度上說,這也是嚴複自己一出胸中憤懣。就在兩年前的那個寒冬,嚴複回到福州,參加鄉試。這是嚴複第四次,也是最後一次參加鄉試。這一次,他依然铩羽而歸。在寫給友人的詩作中,他自怨自艾道:
“四十不官擁皋比,男兒懷抱誰人知?藥草聊同伯休賣,款段欲陪少遊騎。
君來渤海從去春,黃塵埃垓愁殺人。末流豈肯重儒術,可憐論語供燒薪。”
1895年成為了嚴複命運的轉折點,科場失意被水漲船高的社會名望所彌補,四篇論說的刊布以及《天演論》的譯成,讓他名聲大著。他因此結交了諸如梁啟超、張元濟、汪康年等一眾革新人物。從這一意義上說,如果將19世紀末的中國比作一個競技場,那麼嚴複依靠自己過人的天資與敏銳的洞察力在這場救亡圖存的競技中一路披荊斬棘,拔得頭籌。身為一個福州貧寒之家的醫生之子,他的每一步幾乎都是靠自身努力才能走到如今地步。
或許在嚴複自己看來,他就是天演進化之道施於人類社會最好的例證。不過,另一件小事似乎卻證明了退讓不爭同樣也是社會運行的規則——盡管這一規則在嚴複身上多少有些惺惺作態。1896年,就在嚴複因為他的論說和《天演論》的譯作聲名鵲起之時,他給四弟嚴觀瀾的信中,再度牢騷滿腹地抱怨自己想要退隱歸鄉:
“眼前世界如此,外間幾無一事可做,官場風氣日下,鬼蜮如林,苟能拂衣歸裏,息影蔽廬,真清福也。”
分成兩半的嚴複:被誤解的“天演”,被銘記的“富強”
退化
過去的十六年間,嚴複成功地將自己和“天演”“進化”“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些新式名詞和概念捆綁在一起。也讓他成為了那個時代最時髦的人物之一。近代報人包天笑曾在1905年為嚴複舉辦了一場“名學演講會”。他細致入微地描述了嚴複登場時的情景:
“本來約定是下午兩點鍾的,但到了三點鍾後,嚴先生方才來了。原來他是有煙霞癖的,起身也遲了一點,飯罷還需吸煙,因此便遲了,他留著一抹濃黑的小胡子,穿了藍袍黑褂(那時候沒有穿西裝的人,因為大家都拖著一條辮子),戴上一架細邊金絲眼鏡,而金絲眼鏡一腳斷了,他用黑絲線縛住了它。他雖然是福建人,卻說的一口地道的京話。他雖是一個高級官僚,卻有一種落拓名士派頭。嚴先生講得很安詳,他有一本小冊子,大概是摘要吧,隨看隨講,很有次序。”
但包天笑也發現,坐在台下的那些聽眾,“不是聽講,隻是來看看嚴又陵,隨眾附和趨於時髦而已。”
《天演論》雖然是嚴複最膾炙人口的譯著,但恐怕就像這場演講會一樣,絕大多數人對此隻是一知半解地附和趨時而已。他們未必理解嚴複在翻譯時苦心孤詣暗藏的那些機鋒,那些他試圖傳達給讀者的深刻意旨,包括被他刻意偷換的觀點和概念。就像一本書在出版之後,作者就部分地失去了解讀它的權利——唯有讀者才有權聲稱自己從書中究竟讀到了些什麼。哪怕隻是人雲亦雲道聽途說的觀點。
因此,即使將天演-進化這些概念取回中土的嚴複本人,也無法把握它們在中國的發展方向。當革命黨人將天演、進化與革命捆綁在一起推出時,他似乎也找不到合適的反駁理由。
“革命者,天演之公理也。”
鄒容在《革命軍》的這句話,以一種不言自明的奇特方式,將進化論與革命結合起來。革命被革命黨人視為進化的手段,用以批駁反革命的觀點。《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章太炎更引用嚴複早年闡發的民智論,與進化論競爭之說一起打包裝進革命的口袋裏:“人心之智慧,自競爭而後發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開之,而但恃革命以開之。”
革命作為進化的必要手段,不僅不容置疑,更可以突駕躍進。當康梁指出“各國皆由野蠻而專製,由專製而君主立憲,由君主立憲而始共和,次序井然,斷難躥等”時,孫文隻用一句:“是反夫進化之公理也,是不知文明之真價也”便輕輕駁倒了。
甚至嚴複本人,也無法反駁這一由他親手構建起來的進化大廈。錢基博記錄了一件嚴複與孫文之間會麵的軼事,那是在1905年,嚴複因事赴倫敦,孫文聞聽嚴複到來,於是特意前去造訪這位“天演哲學宗師”。當嚴複向他痛陳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急需從教育下手改善時,孫文這位篤定的革命家隻是回答說:
“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思想家,我乃實行家也。
從此二人不再相見。

描繪革命軍與清軍在漢口城內鏖戰情景的彩色版畫《南北軍大會戰之圖》。
“依我愚見,有一點可以肯定,即如果革命黨人輕舉妄動並且所做過激的話,中國從此將進入一個糟糕的時期,並成為全世界的亂源。直截了當地說,按目前狀況,中國是不適宜於有一個像美利堅那樣完全不同的、新形式的共和政府的。中國民眾的氣質和環境將需要至少三十年的變異同化,才能使他們適合建立共和國。共和國曾被幾個輕率的革命者,如孫文和其他人竭力倡導過,但為任何稍有常識者所不取。因此,根據文明進化論的規律,最好的情況是建立一個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製,但受適當的憲法約束。”
武昌起義爆發的一個月後,1911年11月7日,嚴複給《泰晤士報》駐華記者莫理循寫下了一封長信。在信中,他再一次駁斥孫文這位實行家的革命觀,並且援引了他最嫻熟的進化論作為論據。他懇請莫理循發揮他的影響力,說服列強采取一致行動,“為了人道和世界公益起見,提出友好的建議,讓雙方適可而止,進行和解”,因為對立如果持續下去,那些搖擺不定的邊疆地區,很可能會淪入附近某個強國之手。
“一旦出現這種情況,分裂中國的老問題就來了。願蒼天保佑我們免受浩劫!當最壞的事情發生時,任何自詡文明開化的人民都負有責任,因為他們具有阻止浩劫發生的能力。”
就在寫下這封信的同一天,江浙宣告獨立,深受震動的北京官員開始紛紛攜家逃難。嚴複眼看著新成立不久的橡皮圖章的民意機關資政院裏的議員們,紛紛作“鳥獸散”。
盡管嚴複被革命黨人視為思想家,但他依然想用自己的思想去踐行他在信中所說的“讓雙方適可而止,進行和解”。12月11日,嚴複作為南北和談代表趕赴革命中心漢口。在那裏,他發現民眾對清軍攻打武漢時的焚燒行徑大為不滿,“民心大抵皆向革軍”。而更讓他啼笑皆非的是,本來這趟和談不僅花錢甚多,而且路過戰區,一派蕭索,原先委派代表也不過二十餘人,但嚴複發現,“京官爭鑽同來,乃至五十餘人之多,隨從倍之”——難道這些人還想再借機鑽營一番,“豈事成尚望保舉耶?”
即使果真如此,這也是這些人最後一次鑽營了。一個月後,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詔退位。孫文在得悉清帝退位的消息後,兌現承諾,主動辭去臨時大總統職務,讓位給袁世凱。後者為了穩固在北京的軍隊和統治地位,暗中在京津兩地策動兵變,被鼓動起來的士兵四下劫掠焚燒。
新生的民國即以這種暴戾而荒誕的方式開場。身處北京的嚴複,悲哀地發現自己所有悲觀的預言正在成為最慘淡的現實:英國人對西藏垂涎三尺,俄國人對外蒙古和新疆虎視眈眈,而17年前在甲午海戰中一戰稱雄東亞的日本,則迫不及待地將魔爪伸向東北白山黑水之間的萬裏沃野。而在他的眼前,則是各種政治勢力競逐的北京,為了在競爭中獲得勝利,無所不用其極——嚴複眼中,這場革命的唯一成果,就是將這個國家變成了一個貨真價實的弱肉強食的競爭場,一個最粗暴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試驗場。
1912年3月16日,嚴複在北京寫給德萊格博士一封信,這位英國學者很好奇究竟誰是中國第一首國歌的作者:“歌詞確係出自愚下之手,譜曲者名義上是溥侗——溥倫之弟。這件事的過程是這樣的:他們從當初康熙和乾隆帝所譜的皇室頌歌中選了幾個調子,要我根據調子填寫歌詞。樂曲自然現成的,他們所做的唯一事情是把中文的音符改寫成新式樂譜的點和線。”
“這個首都看起來仍然非常殘破淒涼,最令人作嘔的景象,就是你幾乎每天沿街見到那些身首異處的不幸之人的屍體。袁世凱答應給予那些遭到大兵搶劫的人以補償,可是他如何兌現諾言!其目的是安撫那些人,然而我擔心他隻能使那些人更加憤懣。這樣快地失去民心,的確是所能設想的最危險的事。”
在信的最末,附上了這首短命國歌的歌詞:
“鞏金甌,承天幬,民物欣鳧藻,喜同袍,清時幸遭。真熙皞,帝國蒼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革命軍光複南京城,辛亥革命取得勝利。
作者:李夏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