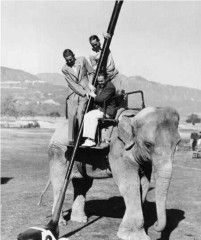瞿宣穎與北京:一位民國“史官”的居京日常
今天知道瞿宣穎的人可能並沒有那麼多。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他寫下了大量文史和掌故學方麵的著作。《北京味兒》一書,便是瞿宣穎關於北京曆史人文、風物、掌故、教育乃至市井社會生活的文章。以下內容為侯磊對瞿宣穎的介紹,也是該書的“代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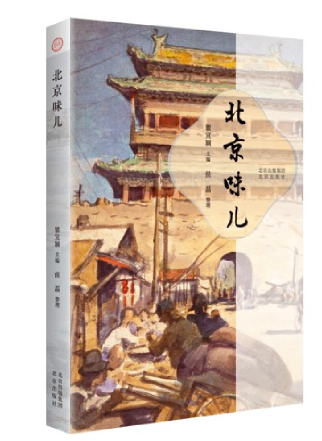
《北京味兒》,瞿宣穎 主編,侯磊 整理,北京出版社2022年6月版。
民國學者瞿宣穎(1894—1973)是有“善化相國”之稱的晚清重臣瞿鴻禨(1850—1918)幼子,在他八十年的歲月中,除了長沙故宅以外,最主要居住地是北京和上海。在北京,他從13歲起進了京師譯學館,精通英文,並學習德文、法文;畢業後去上海讀聖約翰大學、複旦大學,再畢業後北上謀職。1920年,27歲的瞿宣穎進入北洋政府,1946年歸滬獨居,直至1973年死於提籃橋獄中,此間的傳奇,足夠做一篇《瞿宣穎的京滬雙城記》。
他早年居滬時用文言寫作,署名瞿宣穎;壯年居北平時,使用瞿宣穎、瞿兌之、銖庵、瞿益鍇等若幹筆名,從文言、半文言寫到白話;後半生回到上海,寫作時署名瞿蛻園。至今人們尚不易分清那麼多筆名其實是他一人,因為他同時做了若幹方向的學術和文章。
而最終成就瞿宣穎史學家、掌故學家地位的地方,是北京。他筆下躍然紙上的北京,可分為文言、白話兩部分,編成兩部大書。
北平史官
瞿宣穎早年在滬通過張元濟到商務印書館學習,去京後輔助章士釗編輯《甲寅周刊》,並在其上發表了《文體說》《代議非易案書後》。自己開過廣業書社,主編(總編)過《華北》月刊、《國立華北編譯館館刊》《中和》月刊,名列眾多雜誌、叢書編委,眾多詩社社賓,眾多學術機構的發起人和工作主力,眾多學會會員。
他曾擔任北洋政府的若幹官職,而說他是“史官”,是因為他曾擔任以下三個職位:政事堂(國務院)印鑄局局長,國史編纂處處長,河北省通誌館館長。參照各處的官製簡章,現將職責簡述如下:
國務院印鑄局:“專職承造官用文書、票券、勳章、徽章、印信、關防、圖記及刊刻政府公報、法令全書、官版書籍。”
國務院國史編纂處:“纂輯民國史和曆代通史,並儲藏關於曆史的一切材料。”
河北省通誌館:“向各地征集誌料,編纂《河北省通誌稿》,並要求各地編纂誌書。”
擔任過這三處的長官,能堪比古代的史官了。具體而言,瞿宣穎從史料的采集、編輯、教學,到校訂、出版,都親自幹過,都管理過。
身為史官,為國存史;私人治學,為家存史。他在《南開大學周刊》1928年11月26日第七十二期,發表了《設立天津史料采輯委員會之建議》,提出:“著者在近六七年間,著手搜輯舊京史料。除自著短篇《北京建置談薈》以外,都以資料浩繁,不暇整理,不敢輕言成書。……其時得有官廳的助力,頗得許多珍貴的資料,預計一年以後妥可有一部極翔實的新著問世。然而,政府長官更迭,原議停頓,此種私願也無從實現了。”可見他參考工作中的史料來治學,用私人治學來補官方之缺,並希望人人都有保存史料的意識。可惜此處所指的那部“極翔實的新著”則無從問世了。
他認為:“吾國人於字畫則知珍重,於史料則不甚顧惜,其毀於無知者之手蓋不知若幹矣。”而在《設立天津史料采輯委員會之建議》中,他說:“我們所注意的不單是古代的曆史,更要注意現代的曆史,並且要準備未來的曆史。”
何以是“未來的曆史”呢?他在1945年所寫有關《中和》月刊的《五年之回顧》:“誠以人事靡常,零篇墜簡,一旦澌滅,良可痛惜。得一刊物為之傳載,即不啻多寫副本,或幸如羊祜之碑,一沉漢水,一置峴首,終有一傳耳。”而與此觀念不大相同的,是他的三代世交陳寅恪。陳寅恪始終不研究近代史,直至晚年,才在已部分散佚的《寒柳堂記夢(未定稿)》中談一點家事。
與此相符的,是瞿宣穎熱心於參與各種學術組織。七七事變以後,北京古學院成立於北海的團城,於1946年8月裁撤。由江朝宗擔任院長、張燕卿擔任副院長、瞿宣穎與吳廷燮、葉爾衡、田步蟾、周肇祥、王養怡、胡鈞、郭則濂等為常務,所參與者皆為一時名士。學院創辦了《古學叢刊》《課藝彙選》,仍舊使用文言文,每一期都請人題寫刊名。瞿宣穎從第1至5期,連續在其中的《文錄》欄目發表文章,並且參與搜集了眾多前人未刊的書稿,由郭則沄編印了《敬躋堂叢書》。

瞿宣穎 (1894~1973),別名益鍇,字兌之,簡署兌,號銖庵,晚號蛻廠、蛻園。湖南善化(今長沙市)人。晚清軍機大臣瞿鴻禨之子。畢業於上海複旦大學。早年任北洋政府國務院秘書、國史編纂處處長、印鑄局局長、湖北省政府秘書長等職。後在南開大學、燕京大學、清華大學、輔仁大學任教。解放後任上海市政協委員。精詩詞書畫,尤擅於文史掌故,是深具國學功底的文學家和史學家。著有《漢代風俗製度史前編》《漢魏六朝賦選》《北平建置談薈》《北平史表長編》《同光間燕都掌故輯略》《中國社會史料叢鈔》《方誌考稿甲集》《長沙瞿氏叢刊》《補書堂討錄》等豐富著述。還著有《燕都覽古詩話》,為詠覽燕都之作,以詩係文,詩文並茂。其中有關什刹海地區的詩文有15篇。
他對官方的學術機構盡職盡責,且有著很強的期待。在《文化機關的責任》一文中寫道:“凡是負責經營文化事業的人,應該忘懷於一時的政治現象,而竭力發揮所謂為學術求學術的精神。說一句充類至盡的話:縱使國亡,而我們的事業卻不可以中斷。因為我們的事業實在是國家複興的基礎。”
如果官方機構不夠完備,他會加入別人組織的學社,如他參與由表兄朱啟鈐創辦的中國營造學社並編纂史料,所著《明岐陽王世家文物紀略》由中國營造學社出版。而《中國營造學社彙刊》是請他的母親傅太夫人題寫刊名,署名“婉漪”。就在參與古學院的同時,瞿宣穎在自己家中還成立一個學社——國學補修社,參與者除他自己,還有徐一士、謝國楨、柯昌泗、孫念希、劉盼遂、孫海波等,聚會多是在瞿宣穎的半畝園。由大家輪番講授國學知識,他把自己所講的授課筆記整理為《修齋記學》,連載於《中和》月刊,並印成線裝鉛印本出版。
士大夫自由結社琴棋書畫、交遊論學的思路,是他家中世代的生活方式,他不會改變這種方式。
應該編纂一部當下的誌書
民國時熱愛北平的文人大有人在,而瞿宣穎的熱愛遠不止寫幾篇舊京夢華錄,而是把職業前途都用在熱愛上。鑒於北平曆代方誌都不夠完備,應該編纂一部當下的誌書。他想給北京做地方誌。他在《國史與地方史》一文中說:“我們現在固然要一部極好的國史,尤其先要有幾部極好的地方史。”地方史不僅作為鄉土教材培養人們熱愛家鄉的感情,更是國史的一部分,愛鄉便是愛國。
而他與此相關的職位,是在天津擔任河北省通誌館館長,主持編纂《河北通誌稿》,並就編纂事宜與王重民、傅振倫等學者通信,也曾擔任上海市通誌館籌備委員會專任委員,負責上海通誌館的籌備。就私人治學上,他在天津方誌收藏家任鳳苞的天春園中飽覽上千部方誌,著有《方誌考稿》《誌例叢話》等。不論是風俗製度史還是方誌學,都埋藏治掌故學的重要史料。這些,都是他為北平編纂史誌的準備。
而具體工作,他是先後兩次通過不同的學術機構,以及他在機構中擔任的職位來實行的。
1929年9月,國民黨元老李煜瀛(李石曾)倡議成立“國立北平研究院”並擔任院長,這是個相當於“中央研究院”的學術機構,是現在中國科學院的前身。北平研究院下分若幹研究會,也有院士製度,叫作“會員”,一共有九十位。瞿宣穎是史學研究會會員之一,地點位於中南海懷仁堂西四所。史學研究會有眾多學術項目,首當其衝者是編纂《北平誌》,為此還創辦了《北平》雜誌。
也許是學術帶來的興奮,瞿宣穎率先拿出了《北平誌編纂通例》《北平誌編纂要點》,列出《北平誌》要分為六略:一、《疆理略》;二、《營建略》;三、《經政略》;四、《民物誌》;五、《風俗略》;六《文獻誌》,算是定了個體例的初稿。又幹脆自己編了本《北平史表長編》,都發表在《北平》雜誌上。但這部《長編》限於寫作條件,他並不滿意,也曾受到過其他學者的議論,晚年時還對弟子俞汝捷談起過,很遺憾沒有再版修訂的機會了。後來因為抗戰,《北平誌》的編纂工作被迫停止了。《北平》雜誌隻出版了兩期。
另一次是到了40年代,由民國時清史館總纂吳廷燮主持編纂《北京市誌稿》。這部大書共有400萬字,直至1998年才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這一次瞿宣穎擔任分纂,親自編纂《北京市誌稿》的《前事誌》,“采用編年體,為上古至民國二十七年的北京大事記。”《前事誌》原八卷,可惜如今僅存《清上》一卷了。
此時北洋政府的各大機構,官員工資並不低,公務相對清閑,不少人再兼幾個閑差,或到大學裏教書,有的月收入能達上千元。魯迅、胡適等人都買得起房子,以保證學術和生活的體麵。而街麵上的警察或“駱駝祥子”月薪6元,租一套十幾間房的三進四合院不過幾十元,而全買下來需要近千元。此時的北平有古典的遺韻尚無現代化的破壞,有南方的秀麗且有北方的壯美,有皇城府邸的尊貴又有市井小民的竊喜;有廉價的飯食書籍尚無過多的機構冗員,有政府的高工資尚無政治的高壓。瞿宣穎的生活,理應十分滋潤。
然而,這位史官的居京生活是樸實的。父親瞿鴻禨不大愛吃肉,多以素食為主,瞿宣穎也受此影響,並不是位老饕。他懂美食和生活品質,作有《北平曆史上之酒樓廣和居》《北京味兒》等文,不論是寫涮羊肉還是譚家菜的魚翅,皆得其中三昧(當然現在不該吃魚翅了)。但他並沒有過分追求,隻是從小生活水平較高。他筆下的北平,是“麵食與蔬菜隨處可買,幾個銅子的燒餅、小米稀飯、一小碟醬蘿卜,既適口又衛生。……藍布大褂上街,是絕不至於遭白眼的”。至於梨園鼓吹、鬥雞走狗、聲色犬馬,則沒什麼興趣。他寫過篇《記城南》,但他不熱衷於逛天橋看打把式賣藝。誠然,平民娛樂也絕非低人一等,能如王世襄寫架鷹、唐魯孫寫美食、張次溪寫梨園、連闊如寫江湖買賣道兒上“金皮彩掛評團調柳”的人更為金貴。瞿宣穎並非不懂這些,也偶爾會談及一點,但學術興趣並不在此。這一點上他很像周作人,僅以故紙堆自娛。
因此瞿宣穎的掌故不集中在吃喝玩樂、風土人情上,而是將曆史事件、曆代典章信手拈來,本質上是在寫政治製度和風俗製度;更本質上,則是他史學研究和編方誌的副產品。今人的“豆腐塊”味道不如前人,是因為隻有副產品,而缺少治學的主幹。
極為熟悉舊京古籍和曆代名家日記
盡管瞿宣穎在北京住過很多地方,如他住過北池子、住過東四前拐棒胡同17號,1924年其時寓所已遷黃瓦門織染局6號,在京郊住過香山碧雲寺,而他住得最久的地方始終是位於弓弦胡同內的牛排子胡同1號的半畝園東路,前後共四進院落,現在屬黃米胡同。
這所不小的宅院原先是《鴻雪因緣圖記》的作者,江南河道總督完顏麟慶(1791—1846)的故居,東部為住宅,西部為花園,瞿家隻占東部,是瞿鴻禨時代置辦下的。瞿宣穎讀書求學,並生兒育女,直至兒子在這裏結婚,孫子在這裏出生,並最終與妻子離婚,並單人於1946年赴上海(家人在1948年去上海),後陸續將半畝園東路賣出。他寫過《故園誌》,請齊白石畫《超覽樓禊集圖》。長沙故宅中有兩株海棠,而黃米胡同宅中仍有兩株海棠,他請黃賓虹繪《後雙海棠閣圖》,並請郭則沄、黃懋謙、傅增湘、夏孫桐等《為兌之題雙海棠閣圖卷》題詩。
他是《人間世》《宇宙風》雜誌的作者,《旅行雜誌》《申報》月刊、《申報·每周增刊》也是他的發稿陣地,對於北平,他有太多的話想說,且把一切讚美之詞留給了北平。他寫道:“我是沉迷而篤戀故都的一人。”“舒適的天然環境,實是最值得留戀的。”“要找任何一類的朋友都可以找得著的。”“北平有的是房屋與地皮,所以住最不成問題。……生活從容,神恬氣靜……”他認為北平如果以公元938年遼太宗定幽州為南京,到1938年已經是建都一千年了。作為千年故都,北平必應當隆重慶祝,大書特書,且需要整理的學術遺產太多了。
《宇宙風》在1936年第19、20、21期,出過三期《北平特輯》,每輯都是名篇輩出。第19期前四篇文章為:周作人的《北平的好壞》(署名:知堂)、老舍的《想北平》、廢名的《北平通信》、瞿宣穎的《北遊錄話》(署名:銖庵)。《北遊錄話》采用銖庵(作者自己)、春痕(摯友劉麟生)二人對話體的形式,分成十章連載十期,寫銖庵帶著春痕遊覽並談論北京。而第十章《北平的命運》從未來發展的角度,表達出瞿宣穎對抗戰前北平命運的擔憂。在他心中,北平不隻是文化古城,更是近代學術的中心,自古以來有著士大夫自由講學的傳統。而麵對日本的侵略,“以此為中國複興之征兆,亦未可知啊!”這三期特輯的文章被陶亢德編成一本《北平一顧》出版。也許是《北遊錄話》太長,並未收錄。
瞿宣穎喜歡實地考察和旅行,他熱愛地方風物,每到一處都要走訪文物古跡,恨不得立刻研究當地風土。他為張次溪《雙肇樓叢書序》作序稱,張次溪研究北京能“親曆閭巷,訪求舊聞”,他自己也是如此。他寫有《燕都覽古詩話》,每一處景觀作一首舊體詩,並引用舊京古籍講解論述。京城的中山公園、什刹海是他與友人遊覽、品茶的地方。故宮、皇城還是各皇家建築,他都曾親赴考察,並感慨大量清宮中沒有算作文物的日常生活用品,都已殘破丟失(這在當時人眼中不算文物)。他讚同朱啟鈐修改北京的前門樓子,認為這是成功的、現代化的修繕。而到1924年前後,市政公所幾乎拆光了北京原有13公裏的皇城城牆,他對此大為遺憾。皇城城牆今天隻剩下1900米了。

《燕都覽古詩話》,瞿兌之 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