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梵高,最大的意義是解放自己
藝術是無盡的,正如“詩無達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認知,而有趣的靈魂是無法複製的。讀梵高,最大的意義是解放自己,在他畫出的向日葵的金色光芒中,我們都要想一想:如果遇上他那樣的困厄,我們將如何開辟人生?
——梁永安《〈渴望生活:梵高傳〉導讀》
1890年7月27日午後,法國巴黎郊外的奧維爾小鎮,一個麵色嚴峻的男子走上小山,坐在一棵樹下,遙遙地望著陽光燦燦的麥田,滿眼惜別的傷痛。一會兒他走下山坡,踏進熱氣騰騰的耕地,漸漸舉起一把左輪手槍,壓向胸部,決然扣動扳機,轟然倒下。四個小時後,他從昏迷中醒來,帶著渾身血跡,搖搖墜墜地走回了暫住的旅館。三天之後,他握著弟弟的手,黯然去世。
他就是溫森特·梵高,一個視藝術為信仰,以生命為火把,在暗影重重的人世間負重前行的探尋者。

源自電影《至愛梵高·星空之謎》(2017)
他去世於最不該隕落的時刻,他正處於藝術的新起點,他死在三十七歲,繪畫生涯僅僅十年,畫了864張油畫,1037張素描,150張水彩畫,其中有36幅自畫像,11幅向日葵。終其一生,除了少數繪畫圈裏的人,公眾對他一無所知。然而也正是在1890年初,他賣出了有生以來的第一幅畫,得到四百法郎。青年美術評論家奧裏埃在《法蘭西信使》雜誌發表了一篇評價梵高油畫的文章,熱烈讚揚梵高的畫作具有“非同尋常的力量和強烈的表現力”。同時奧裏埃也痛感惋惜地長歎:
“這位有著一顆發光的靈魂的堅強而真誠的藝術家,他是否會享受到被觀眾賞識的快樂呢?我想是不會的,與我們當代資產階級的脾性相比,他太單純了,同時也太微妙了。除了得到與他誌同道合的藝術家的理解,他將永遠不能為人所完全接受。”
奧裏埃完全沒有預計到,梵高身後的藝術生命如悄然掀動的海嘯,初始水波不興,漸漸波浪湧起,迅疾驚濤拍岸,一百餘年間冰火兩重天。梵高去世後剛剛半年,1891年1月25日,他最親密的弟弟提奧也黯然離世。弟媳婦喬安娜繼承了梵高的大部分畫作,她深深沉浸於梵高畫作中的熊熊激情,立誌一生推廣梵高的作品。她在提奧去世後的十年間,舉辦了七次梵高畫展。盡管展覽門庭冷落,她依然不改初心。直到第七次,馬蒂斯等一眾巴黎的繪畫大咖前來觀瞻,引起公眾的矚目,終於將梵高的泣血之作推向了藝術圈的視覺焦點。1915年之後,梵高的單幅畫作售價達到三十萬法郎。
1.為梵高寫一本傳記
那是在1927年春,年輕的美國人歐文·斯通(IrvingStone,1903—1989)來到法國,經友人的推薦,去巴黎的盧森堡畫廊參觀梵高的畫展。畫廊展出了梵高的70餘張油畫,歐文·斯通仿佛踏入灼日之下的宇宙幻境,完全被震撼了。五十五年之後,他還驚歎不已地回憶:
“在色彩的輝映下,就像陽光透過彩繪玻璃照進大教堂一樣,波光流瀉,色彩斑斕。對於受過意大利宗教畫和巴黎寓意畫過多熏陶的我來講,繪畫已經成了一種不能令人激動的藝術。然而,此刻,突然間麵對著溫森特的這個由色彩、陽光和運動組成的騷動不安的世界,我的確驚呆了。當我驚詫不已地徘徊於一幅又一幅壯麗輝煌的油畫前時,我進入了一個新的境界,整個世界豁然開朗:在人、植物、動物從那富有生命感的大地升向富有生命感的天空和太陽,然後又向下彙聚到同一中心的運動中,一切生命的有機成分都融合在一起,成為一個偉大崇高的統一體。”
也就從這一天開始,歐文·斯通心潮奔流,越來越克製不住一個澎湃的心願:要為梵高寫一本傳記。三年後,他毅然決定動筆。雖然他深知自己麵對梵高“最為悲慘然而成就輝煌”的一生,有太多需要探索的生命秘境,但他無法離開被梵高“迷住了”的心境,在“幾近發狂”的高亢激情中,不分晝夜地寫了半年,最後寫出了這本42萬字的厚重之作。這本書費盡周折出版後,長銷不衰,在全球售出各種語言版本將近三千萬冊。
筆者是在1985年第一次讀到歐文·斯通的這本傳記,幾乎是通宵讀完,從此難忘。這次重讀這一新版《渴望生活:梵高傳》,恍然三十七年過去,竟然正好與梵高的生命長度相等,感歎不已。懷著深深的敬意,細細又讀了三遍,書頁上畫滿了橘色的記號,時時感覺以前沒有讀過這本書,一個全新的梵高從文字的斑駁中忽明忽暗地跋涉,恍若一個不羈的旅者在時光中奮力地尋找,尋找那朵夜空下熠熠閃爍的大葵花,尋找金色麥田中嬉戲的精靈。
他一生在探尋什麼?他如何撥開世俗的煙塵,衣衫襤褸而又精神豐足地前行?他如何經受了生存的碾壓而不變形?……一切的一切都是巨大的追問,催促著蕩人心魄的閱讀——不,不是閱讀,是對一個滾燙的純粹靈魂的撫摸,是一次於無聲處的漫長修煉!
最動人心魄的是,梵高坎坷情路上的顛沛流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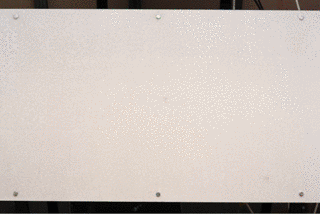
源自電影《至愛梵高·星空之謎》(2017)
2.在愛情、繪畫背後,他最虔誠的奉獻都給了誰?
按理說,撰寫梵高這位經典大師的生平,應該從荷蘭南部的小鎮鬆丹特寫起,這是梵高的家鄉。然而歐文·斯通並沒有沿著這條從小到大的時間線順向描寫,一開篇設置了一個“序幕”,寫的是倫敦時期的梵高。
那是1874年,他二十一歲,正在這座大城的古比爾公司倫敦分公司工作,專職推銷繪畫和藝術品。他雖然年輕,卻已經在畫商的行業裏曆練了五年,每個月能為公司賣出去50張畫片,是一個頗有商業能力的推銷者。但他生活的中心卻不在商業,而是愛情——他愛上了自己房東的女兒烏蘇拉。她十九歲,芳華四溢,“一觸及她那光滑細膩的肌膚,他就心慌意亂”。這太正常了,愛情往往是青年成長的第一課,也是獨立體會人性、人情冷暖的修羅場。
歐文·斯通從梵高的愛情入筆,奠定了這本傳記的基本邏輯:全書起步於梵高的情感與精神發展,而不是日常人生的流水賬。在這部傳記的“序幕”中,歐文·斯通把梵高寫成一個非常陽光、非常純粹、非常單純的青年。他對愛情滿懷信心,抓緊時間向烏蘇拉表白。他覺得自己每個月能掙五個英鎊,在當時的青年中屬於收入很不錯的人群,能夠給烏蘇拉一個像樣的生活,所以他信心十足地向烏蘇拉表白:“隻有你做了我的妻子我才能幸福。”他萬萬沒有想到,烏蘇拉斷然拒絕了他,還說“我訂婚已經一年了”。

照片中最左邊的女子為烏蘇拉



























































